常听到一些人在感叹:当今这社会,除了权力与金钱,还有什么能令我们敬畏?这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很多人对权力与金钱也谈不上敬畏,只是谄媚与贪婪而已。我们现在无论谈论任何问题,最后都会扯到权力与金钱上,连呼吸、饮水、买房、求职、马路塞车、挂号看病、小孩入学,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几乎都离不开权力与金钱的考量,当然也包括文学,包括在这个年代还有没有诗人这样的问题。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这种感觉我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有的,当然,那时我也不是诗人,只是写了一些小说,便常常因写小说而感到羞耻。眼看周围的朋友,个个下海经商,横向发展,拎着个公文箱满街跑,办公司,签合同,数钞票,忙得不亦乐乎,而我却在绞尽脑汁苦想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一类蠢问题,确实是一件值得羞耻的事情,所以当别人问我在忙什么时,我绝对不会说在写小说,只会说:“没啥忙的,没啥忙的,你有什么好介绍,让我也发点小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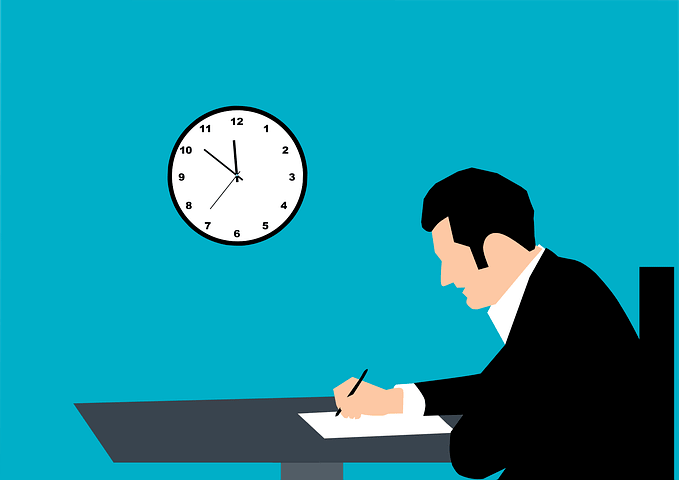
不过,深究起来,这种羞耻感,也许正是基于对文学的敬畏,认为它与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别人无法理解,所以干脆不说,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清高。但到了今天,这种微薄的敬畏恐怕也荡然无存了。米沃什说:“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对抗嘲讽,而是就算你扒光衣服站在公众面前,也没人对你的身体缺陷感兴趣,就算你打锣吆喝,也没人想停下脚步看一眼。这成了另一种羞耻。
这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吗?显然不是。我简直不知道现在残存的文学杂志是怎么生存的,除了图书馆订购,还会有个人订户吗?这个问题我甚至不好意思去问那些杂志编辑。同样,现在的出版社文学编辑是怎样做图书的,说出来也令人沮丧,据说大家都感到江郎才尽了,因为想出任何选题,都会被领导一句:“能赚多少钱?亏本你负责?能拉到项目资金吗?”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现在米沃什以大无畏的姿态挺身而出说:“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他换来的也许是人们的哑然失笑:好啦好啦,哪凉快哪歇着去吧。你以为人们会嘲讽你,已经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人们连嘲讽都懒得了。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这世上的人心是不会死绝的,真正的文学永远会存在。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但有什么依据,我也说不上来。
记得几年前北京举办过几次史铁生作品朗诵会,让我常常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在史铁生那间简陋的房子里和他聊天的情景。他残缺的身体并不能困住他澎湃的文学热情,这让我长久地感动。当然,如今已没多少人记得这位身残的诗人了。这也是我读到米沃什这段话——“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时,在脑海里出现的一点淡淡的痕迹。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