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末的周日夜晚,橱窗贴满圣诞装饰的太古汇灯火通明,旁边的超级文和友一如既往地打着昏黄的灯光,刻意又倔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市井气”。
“风筒辉?早就不做啦!”“阿婆牛杂”的店员告诉识广。在入驻“市井博物馆”——超级文和友太古汇店(以下简称“文和友”)不足两个月后,文和友的“招牌”商户之一——风筒辉选择离开。
不止风筒辉,“博物馆”里的其他“展品”也在快速变换:7月份开业至今,盲公丸、风筒辉烧烤、唐氏秘制烧鸡翅、猪扒一哥酸辣米线都相继离场。4个月前,这个热门打卡点凌晨1点还在排队,如今在周日的晚上,叫号处的屏幕泛着冷冷的绿光:“等位桌为0”。
名角退出,观众渐乏,超级文和友的市井大戏为何不吸引人了?

离场与冷场
“我是自己想走的。”接受识广采访时,风筒辉说。
“每天早上4、5点我就会开车运货到文和友,但那个时间段,天河路总是塞车。”风筒辉第一次接触文和友这种“市井/实景版大食代”的商业模式,颇为不适应,“备货的分量难控制,有时多了,有时少了。”
分身乏力是风筒辉最大的感受。当时,风筒辉和另一个伙计负责运营分店,但顾得了这家,就顾不了市二宫的门店。
其实“和平分手”的说法是给彼此留个面子。虽然超级文和友店租、水电全免,只按比例收提成,风筒辉还是认为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9月份就径直关店,专心做好总店。
前后加起来,风筒辉在文和友只开了两个月。

文和友里还留着风筒辉烧烤的广告纸
在文和友,风筒辉占据入口的黄金位置,所以其“消失”也显得特别惹眼。在消费者不容易留心到的文和友内部,更多店也悄然更换。
在风筒辉之前,同样开在一楼的盲公丸选择离开;原来在二楼的特色纹身店,现在竟然已经变成了福彩销售点;驻扎于2、3楼的猪扒一哥本来在文和友有三家店:唐氏秘制烧鸡翅、阿一猪扒酸辣米线店、新斗记,在11月之前,鸡翅店就已经关闭。
11月22号,识广去到酸辣米线店采访,店员透露,酸辣米线店和烧鸡翅店每日流水已远远不足1万,“生意不好,老板就把烧鸡翅店关掉,省点人力物力。”不到一个星期后,识广再次来到文和友,酸辣米线改朝换代,挂上了“耕田公”的金漆招牌,既卖凉茶,也售糖水。店面的玻璃窗上,四张A4纸拼在一起:“本店29号 新张营业”。

客流变少、生意不好,是商铺离开文和友的主要原因。
7月份刚开业的时候,荔银肠粉每日流水有5、6万元,“炒粉的铁锅都炒烂三只”。但不到3个月,每日流水就降至2万左右。
荔银肠粉的销量在文和友里面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旁边刘福记每日流水在1万上下,与阿婆牛杂、炒螺明、陈添记鱼皮相似。
刘福记的伙计阿杰(化名)打趣道:“现在每日的生意怎样,完全预料不到的。”至于原因,阿杰(化名)说,“这里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大家都是只拍照,不消费。”
破碎的营销叙事
虽然商业体里店铺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现象,但文和友内部店铺的变化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仍然让人意外;尤其是风筒辉的黯然离场更是意外中的意外。
作为一个外来物种,文和友在广州“市井博物馆、城市烟火气”的营销叙事由两套密不可分的符号系统构成——一套就是其做旧的建筑设计风格;一套就是其引入的本地商户,其中尤以“广州地摊三杰”(阿婆牛杂、风筒辉、炒螺明)最为重要。如果说前者不免显得做作的话,后者无疑比前者更能让人对文和友的“情怀叙事”多几分信任和尊重。
但现实却是,这套营销叙事正在变得“外强中干”。
建筑风格上,无论是长沙的超级文和友,还是广州的超级文和友,都用80、90年代的红砖房混搭50年代单位宿舍,90年代广州的7位数电话号码配衬繁体字标语,褪色的锅碗瓢盆,碎掉的花砖,窗台上挂着的白色汗衫,建构其市井叙事。

在足够充分的讨论之下,已成共识的是:文和友并非在复原某个时期或某个片区的广州,只是用一套通行的符号编码营造一种年代感。
做旧的建筑是文和友讲述市井故事的框架,而故事的内核或者说真正的广州特色隐藏在文和友引入的本地商铺中。
超级文和友总经理翁东华接受36氪采访时说,在流动摊贩普遍被驱逐的处境下,文和友“为商户解决生存问题和传承问题”,为摊贩提供收容之处,继而“传承市井文化、保留城市烟火气息” 。
但文和友收容的并非那些无处容身的“走鬼档”,而是收容名气和销量在某个尺度之上的、从众多地摊中业已脱颖而出的“走鬼”。生存问题在他们身上并不成立,他们亦不需要文和友“拯救”;真正的面临生存危机而同样具有广州特色的“走鬼”可能入不了文和友的法眼。
换句话说,和建筑设计的思路一样,文和友精心挑选的是广州的一些市井商业“符号”:阿婆牛杂、风筒辉、炒螺明的招牌就像文和友打出的广告牌,是它营销叙事得以成立的根本,是它能够“引爆”广州的火药。

从商业上来说,文和友的市井文化注定是一场被豢养出来的文化景观,非关现实。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我们对文和友有太多道义上的期待。必须承认,即便只是引入一些“符号”,能让风筒辉、阿婆牛杂、炒螺明等广州地摊代表在城市的中心商业区有一席之地,给予租金、宣传(文和友有拍摄《街头大厨》)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增加收入,仍然不失为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现实的残酷在于,无论文和友还是商铺,最终极的检验来自市场,考核这套营销叙事是否有效、有效期有多久的不是公众号阅读量,而是销售额数字。
生意讲的是投入和产出效率,如果风筒辉不能创造和其铺位位置相匹配的收益,文和友还能有多大的耐心把租金和分成上的损失权当广告支出?反过来讲,如果文和友不能带来与投入的时间、原材料、人力、分成成本相匹配的预期的收入,风筒辉们又有多大的耐心继续当文和友的广告牌?
在帮助文和友完成打开广州市场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后,面对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正比,风筒辉选择“体面”分手。但这是否会让文和友本就不牢靠的营销叙事显得更加空洞?是否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速文和友的“冷却”?
不得而知,至少风筒辉的离开和更多商户在短时间的快速更换,以及文和友的快速“遇冷”,表明文和友的营销叙事已经失去了“横空出世”时的魔力,也再次证明了广州消费者的精明和务实。
相似的困境
正如在上文已经表明的,对于入驻的部分代表性商户,文和友租金、水电全免并且进行免费宣传,提供了一个低风险开设分店的机会,并非不值得肯定。但地摊商户的升级困境,没有因此消失。
在识广看来,阿婆牛杂、风筒辉、炒螺明身上都有一种特质,一种底层人努力用双手和汗水创造财富,为自己也为家人努力“搏到尽”的坚定和自信,与其说他们的底色是悲凉,不如说他们的底色是励志。

附带一说,识广极为反感将这和城市是否包容扯上关系。难道城市包容,底层人就不用用力生活了吗?
我们尊重和赞赏风筒辉、阿婆牛杂、炒螺明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他们大多数也许并不具备同时经营两家店的能力。
从商业上来说,完成由地摊变成门店(个体户)的转变对于许多地摊来讲还不太难,但由一家店到两家店却是完全不同的挑战:不仅是租金、人力成本的增加,还有出品能否保证统一的问题;对于像风筒辉、阿婆牛杂这些本身已经被故事化的商户而言,还有一个故事能否延续号召力的问题。
阿婆牛杂、风筒辉烧烤、陈添记鱼皮等广州老店,都是从地摊开始做起,在市区开出门店,再被邀请加盟文和友。如何两头兼顾,是商家必须面对的难题。他们在分店和总店之间寻求人力、物力的平衡,保证不会做坏个“朵”。

风筒辉在市二宫的门店
为了统一分店和总店的食物素质,刘福记的伙计阿杰(化名)表示,刘福记的炸云吞、云吞面等食物都是老店的师傅做好,再运到文和友。然而,“为食”的市民阿明吃过招牌美食后,却对识广表示,文和友分店的食物不如老店的出品。识广身边的一个朋友对于阿婆牛杂也有类似的评价。
美食测评大号“企鹅吃喝指南”的评价更有代表性:“……很多店并非老板亲自经营,给人感觉更不real了。像阿婆牛杂的阿婆几乎不出摊,风筒辉平时主要是徒弟驻场…缺失‘人’的老字号,让这份情怀显得有点牵强。”
难道从总店运到了文和友分店,食物就会变味了吗?难道阿婆徒弟的牛杂,就真的跟阿婆的牛杂有那么明显的味道上的差别吗?
也许并不是食物味道上的差异,而是故事性上的差异——很多消费者,对味道的评判不仅来自事物本身,更重要的食物背后的人是否有故事性、有名气。
当地摊被故事成就的同时,也被故事捆绑在“神坛”之上。哪怕仅仅因为故事主人公的缺席,消费者也会认为同样的食物吃在嘴里“缺了点什么”。
利用这些故事树立自己品牌的文和友,也会落入同样的困境。从“排队3000桌,等位4小时”变到无人等位。人们来去匆匆之间,留影数张、po图上网就足够让这趟行程完成使命。故事的魔法减弱之后,人们似乎连消费的兴趣都没有了。
轻易为故事买单,又快速地审美疲劳,这种情况我们见的少吗?又能指责什么呢?消费主义在这一刻透露出一种令人无奈的冷酷。
参考资料
超级文和友总经理翁东华:亚洲最大龙虾馆的故事,36氪,2020.10.
这年头网红小龙虾店这么猛了吗?排队4小时,拍照1小时,吃饭20分钟,企鹅吃喝指南,2020.07.
图片:Uma、Paris
本文在发布前识广有采访超级文和友广州团队,也得到了回复;但由于无法满足对方阅稿要求,按对方诉求,文章并未引用相关回复内容。特此说明。
撰文 | Uma
编辑 | P.K
© THE END
本文由识广原创出品,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互动话题
你会去文和友消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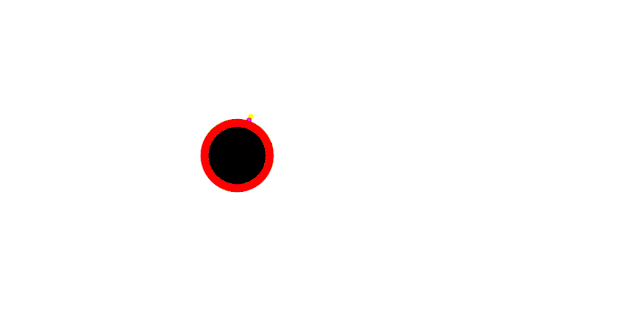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