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广州发电厂控制室里,灯火通明。仪表盘里,一盏盏红色指示灯在不停地闪耀,一支支表针在正常地摆动。强大的电流,通过一条条粗大的电缆,源源不断地输往市区、工矿、农村……”
这是报纸对广州1978年1月1日凌晨的描写。此时街道上静悄悄,只有一串昏暗的路灯,气温在摄氏5、6度之间,北风二级,寒气砭骨。白天最热闹的中山路,现在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在夜色中匆匆行走,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车尾灯逐渐远去。马路两旁边的骑楼,大部分窗户紧闭,没有灯光透出。人们还在熟睡之中。
当海关大钟的指针,跳向5时正时,微光渐渐从东面泛起,天就要亮了。冷清的街道开始人影憧憧,许多老人、小孩在市场门口瑟缩着,排起了长长的人龙,手里捏着一两张皱巴巴的肉票、鱼票,等着买几两肉过节;元旦还要上班的人陆续出门,赶着去搭头班公共汽车和电车;第一班从沥滘驶来的渡轮,在西堤码头徐徐埋岸;广州西郊大队的农民开始忙碌,把六万多斤菜心、生菜、西洋菜、莲藕和马蹄,运往市区各个市场;在悬挂着“实现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标语的街道上,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混合着公共汽车的“吱吱”刹车声、单车的“叮叮”铃声、巷子深处公鸡的“喔喔”啼唱、晨运者跑步的“踏踏”足音,把睡梦中的人都吵醒了。
天真的亮了。街头阅报栏贴出了今天的新报纸,吸引一些早起的人驻足浏览,广州仅有的两份本地报纸《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都在头版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南方日报》第四版刊登了老作家陈残云一篇迎新年散文,激情洋溢地写道:“让我们为迎接一九七八年新的胜利而欢呼歌唱!”

新的一年,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吗?人们好像有所期待,又好像雾里看花。在经历了漫长的高强度政治运动之后,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民间疲惫不堪,蕴蓄着强烈的改变冲动,但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却没人说得清楚。无论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平头百姓,都不清楚,前方一片暝茫,路向不明。有人说,“四人帮”虽然倒台了,但“两个凡是”还是要坚持,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就在几天前的12月26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同时在头版刊登毛泽东的旧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和《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紧接着在1月的《广州日报》上,《跃马扬鞭大干新一年》《以大跃进的精神力争高速度》《粮食高产大有可为》《树立大跃进思想高速度发展我市国民经济》《国营农场要来一个大跃进》等文章,连篇累牍,把“实现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似曾相识的口号,似曾相识的氛围,让人喜忧参半。





虽然“两个凡是”如泰山压顶,却压不住民间求变的反作用力。“文革”既已结束,总得有点变化吧?哪怕只是缓兵之计,也需要有个口子,以释放民间的压力。于是,许多在“文革”中被批判、禁演的电影,像《战上海》《刘三姐》《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景颇姑娘》等,都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仓库里翻出来,重新上映,以发挥安慰剂作用;新电影也在加紧拍摄,这一年推出了《熊迹》《青春》两部,虽然还是一股“文革”腔,但有总比没有强。人们兴奋地涌向新华、新星、解放、中华等大小电影院,以至一票难求。
报纸公布购票规则,元旦期间的电影预售票,一半在售票处公开发售,每人限购五张;其余在工厂密集地区设立临时售票点发售,或委托工矿企业代售,另有少量当天票,专供港澳同胞、华侨和荣誉军人,在特定窗口发售。市民排起了长长的人龙,和买鱼、买猪肉的队伍一样长。所有机关单位、工矿企业的礼堂、球场,凡是能放电影、演戏的,统统利用起来。看电影就像一日三餐,不可或缺,有人一天看三四场电影,放映日本电影《追捕》时,因为实在太过火爆,不少影院将尾场排到深夜2时开映,也还是满座。无论是学校还是肉菜市场,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人在说“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卡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这句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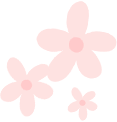

1977年底全国恢复了“文革”中停止的大学招生,全国有570万25岁以下的未婚青年(1966、1967年的高中毕业生年龄放宽到30岁)参加了高考,结果很多已成家立室、有儿有女的人,也去赶考。收到大学体检通知书的人,欣喜若狂地忙着通知亲朋好友,以最快速度收拾行李、照相、办理户口迁移,飞奔向新的人生。
新生还没入学(要到1978年3月才正式开学),1978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又传开了,1977和1978两年合并招收,年龄在35岁以下(后来放宽到40岁),即使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的在职人员,但有“同等学力”(学习能力)也行。“文革”期间毕业的大中学生们,无不怦然心动,纷纷冒着寒风,到市招生办公室打听报考条件,索取招生简章。3月报名,5月初试,6月复试,9月入学。新华书店的售货员发现,在过完“革命化的春节”后,来购买《高等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的年轻人骤然增多。这一年,广东全省招收到约500名研究生,其中108名进了中山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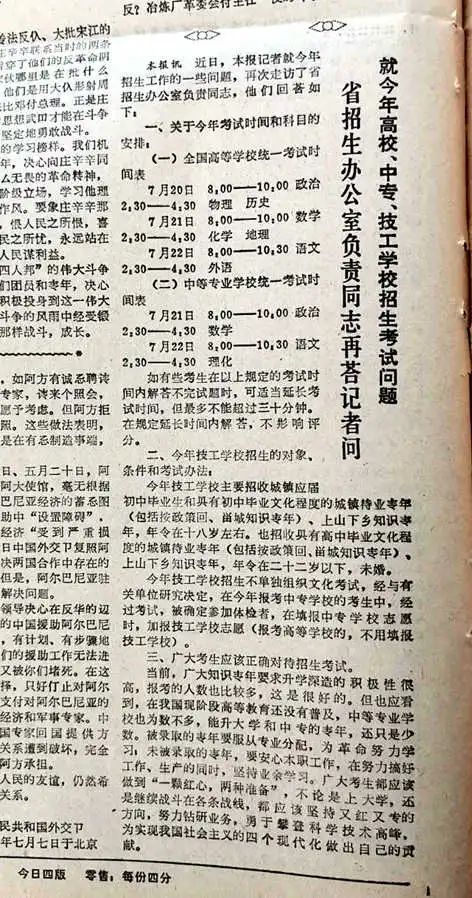

六七十年代被赶去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现在更关心何时可以回城,有人被安排到县城的农机厂、食品站、粮管所、建筑队、民办学校,算是到城镇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如果在前几年,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幸运儿,值得买三两白酒,一碟卤花生庆祝一下,但现在更希望回到大城市,回到广州。高考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但能考上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天之骄子”,大部分人仍然徬徨歧路。
从1978年起,国家不再强制上山下乡了,高中毕业生一律交街道办事处安排,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称,叫“待业青年”。人们都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愈来愈多的知青,丢掉锄头往广州跑,与应届高中毕业生汇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庞大的求职大军。
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运气好的,考上了大学,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运气稍弱的,虽然高考落榜,但被招进了国营工厂,当上“工人阶级”,也算春风得意,学徒第一年工资18块,第二年22块,第三年24块,满师以后每月可以拿到39块,足以羡煞旁人;运气再差点,在父母单位当个临时工,工资每天八毫纸,每餐饭堂三两白饭,五分钱萝卜干炒肉丝,外加几条白菜,被谑嘲为“八路军”。但如果父母有熟人关系,走走后门,转为正式工,也能实现鱼跃龙门的梦想。
剩下运气差到连“八路军”也当不上的人,被鄙称为“社会青年”,他们也要吃饭,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在电影院门口炒卖电影票、兜售明星照片、通俗歌曲词谱,有人跑到虎门,搞些衣服、袜子、太阳镜之类的香港走私货,回广州倒卖;有人在街道摆摊,靠卖凉茶、猪肠粉、绿豆沙,或做些修、补、改的手工,勉强维持生活。新一年对他们而言,别说“跃马扬鞭”,就连马毛都还没摸着。
然而,这是巨变的前夜。
(图片来自网络)







最新评论